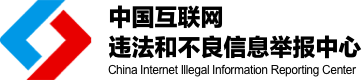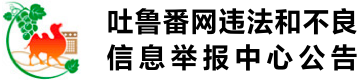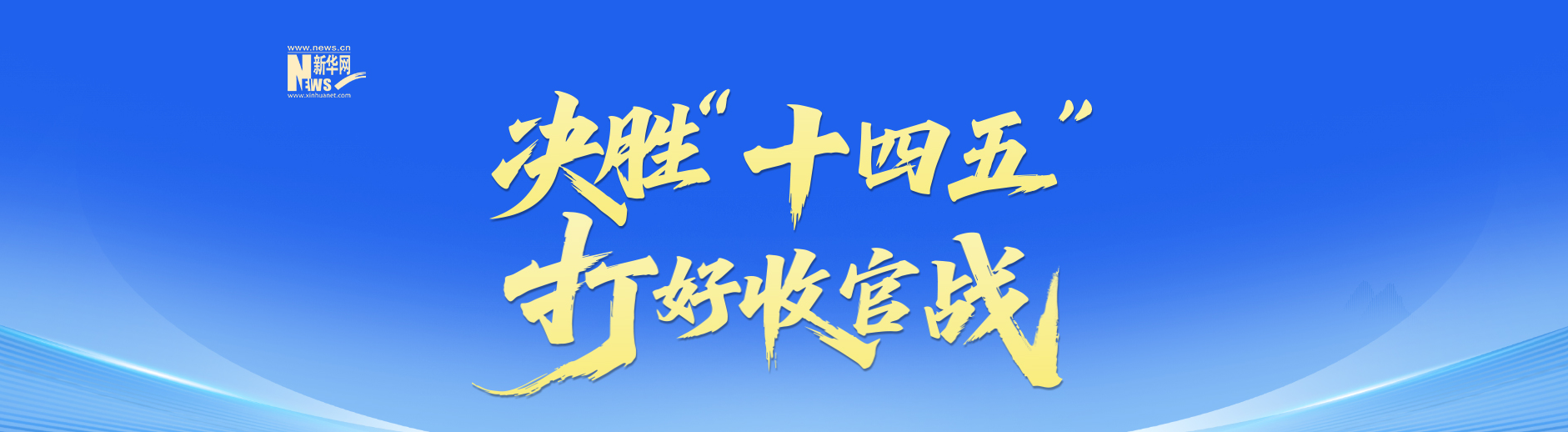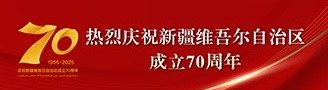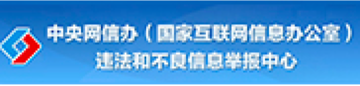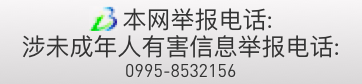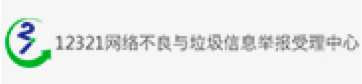一生愛種地的中國人,早在2000年前的吐魯番就種上了
你有沒有發現,中國人似乎有一種刻在DNA里的“種地天賦”?
無論是陽臺花盆里的蔥蒜,還是邊疆荒漠中的萬畝良田,我們總能把腳下的土地,變成生機勃勃的田園。
而今天要講的這個地方,可能比你想象的還要“能種”——
你以為新疆吐魯番只有火焰山和甜葡萄?
紀錄片《吐魯番往事》為我們揭秘,早在2000年前,這里就已是中國人的“西域糧倉”。
漢代名將班勇帶著五百兵卒在此開啟的屯田事業,把“種地技能”牢牢焊在了西域大地上。

一、漢代屯田開先河,吐魯番的“種地基因”有多早?
公元123年,東漢延光二年,西域長史班勇率五百兵卒進駐吐魯番盆地的柳中城。
他不是來打仗的,而是來“種地”的。
為什么選中吐魯番?
“從軍事角度看,吐魯番向東背靠敦煌,具有先天的戰略優勢,進可攻退可守。”
“從屯田的角度來看,吐魯番盆地具有深厚的農業耕種傳統。”
班勇帶來的兵卒中,有不少掌握中原先進農耕技術的人。
他們“趕在第二年下種前播下了他們來到西域后的第一批種子”,到了秋天,“獲得了意料之中的豐收”。
這不是普通的耕種,而是“一手抓軍事、一手抓屯田”的戰略行為。
班勇的目標很明確:“發展好屯田,就有了物質基礎做保障,也就有了跟匈奴人打持久戰的可能。”
就這樣,吐魯番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“軍墾示范區”之一。
漢朝的士兵,一手握劍、一手扶犁,在這片熱土上,種下了西域治理的第一粒“種子”。

二、歷代接力種地忙,吐魯番的“農耕進化史”有多燃?
漢代的屯田智慧,被后來的唐朝接力發揚。
唐代詩人岑參在詩中描繪了這樣的場景:“塞迥心常怯,鄉遙夢亦迷。那知故園月,也到鐵關西。”
而他筆下的交河城,不僅是軍事要塞,更是屯田重鎮。
“正在田間耕作的是脫下兵甲的士卒,他們和岑參一樣來自中原。”
吐魯番出土的文書中,還發現了一件“嚴茍仁租葡萄園契”,記錄了一個叫嚴茍仁的西州人租下兩畝葡萄園,租期五年。
這說明,唐代的吐魯番不僅種糧,還大力發展葡萄等經濟作物,甚至出現了“租地種葡萄”的市場經濟行為。
而這份“種地”的傳統,從漢唐一直延續到現代:1950年,新疆軍區發布命令:“全體軍人,一律參加勞動生產,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勞動生產建設戰線之外。”
駐守吐魯番的四十七團,變成了一支植棉隊。
1954年,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,這支隊伍成為今天仍駐守吐魯番的兵團二二一團的前身。

三、種地背后的深層密碼,不只是“收獲”這么簡單
中國人為什么這么愛種地?
在吐魯番,答案不僅是“生存”,更是“守護”。
從班勇的“以農養兵”,到唐代的“士卒耕作”,再到清代的額敏郡王歸順中央、重建家園,屯田始終是中原王朝穩定邊疆、促進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。
紀錄片中這樣評價班勇的功績:“他繼承了父親‘以夷攻夷’的理念,不勞中原之師,糧草自給自足,以屯田政策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雙重穩固后方,維護了漢王朝的邊疆穩定。”

而今天的吐魯番,依然延續著這份“以農興邦”的基因。
從葡萄溝的萬畝葡萄園,到湖南援疆隊帶來的“紅石榴”品牌,從古代的屯田士卒到今天的援疆干部人才,種地,始終是中國人守護家園、建設邊疆最樸素也最堅定的方式。
今天的吐魯番,依然是那個“瓜果飄香”的豐收之地。
但你若細看,會發現:那不只是甜美的葡萄與哈密瓜,更是兩千年來中國人在這片土地上種下的文明根基。
我們從漢朝一路種到今天,種的是糧,守的是土,連的是心。

正如一位網友的感慨:“中國人的種地,不是技能,是浪漫。”
而這浪漫,早在2000年前的吐魯番,就已寫進了中華民族的基因里。